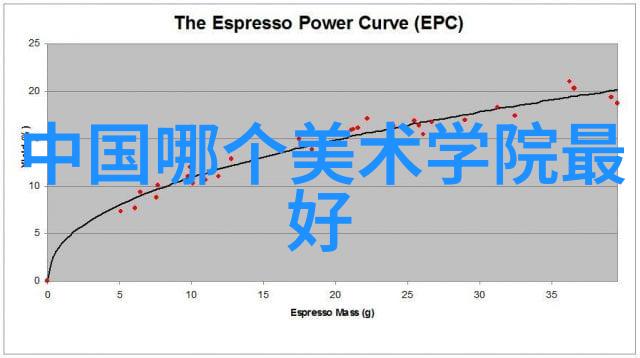前几日,北方一些城市纷纷降下了这个冬日里的第一场大雪,久被灰调笼罩的都市顿时一片皑皑。连续数日,各式各样以雪为主题的照片被人们兴奋地晒了出来。雪后骤至的苦寒中,笔者默想着往昔大雪弥漫下的山容水色和那些与雪有关的寒士故事,这似乎又通往了一个艺术史的话题——雪景山水。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郭熙《林泉高致》)古人骋思栖神于山水之间,假笔墨尽写自然之性,实陈吾侪心曲。山水真乃大物,非静心滤思洁志者,不能纳之于胸壑。山水画为笔墨与造化相生之至境,唯达者方可解其灵旨。细细梳理中国山水画史,有两类主题的山水画历代不衰,即隐逸图与雪景图。学界认为,存世最早的雪景山水画约略可推至传为王维所作的《雪溪图》《江山雪霁图》等几图,其后,范宽、关仝、李成、黄公望等人沿袭有序。至晚明,董其昌等人以王维的雪景山水画为重要佐证标举出影响巨大的“南北宗论”,使文人画史的体系和脉络得以重构。一定程度上,历代诸多山水作品是隐逸和雪景的有机融合,隐逸是超世情怀的传达,而雪景正是其在图像中的实体呈现。 现代都市人拍摄的雪景照片与古人传承不息的雪景山水虽形式载体不同,但却能够依稀折射出一种千古因袭的文化心理。不禁诘问:缘何历代文人钟爱雪景图?深入考证可知,以雪景之清皎托喻心境之高洁,可谓古代文士的一种“比德”观念。这一观念导源于先秦,如孔子以山水和松柏比德、荀子以玉比德等等,都彰显出贤士达人对高洁精神的崇尚与希冀。这般意绪在历代诗文中也多有记述,如谢惠连《雪赋》云:“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不能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平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浩然,何虑何营”,又如孔稚圭《北山移文》言:“夫以耿介拔俗之际,潇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芥千金而不眄”。 再回到画史,从唐、五代及宋初山水画家的地理分布而言,绝大部分画史有载的名家如王维、李思训、荆浩、关仝、范宽、李成、郭熙等都活动于北方,他们也皆作有雪景山水,尽管有些只是在画学著录中保留了画名。郭熙曾形象地描述了山之四季与人之心灵的内在关联:“春山烟云连绵而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而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而寂寂”,足知冬山成就了士人悠然绝尘的“寂寂”襟怀。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对范宽的评语也涉及雪景之思:“居山水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这些史料可证,士人凭依雪景山水“比德”,它不仅包孕着长期的技术性演变,同时又是文人精神的象征性选择,进而成为其寄情遣怀的独特艺术载体。 20世纪的山水画创作较之传统在内蕴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1949年建国以后的30多年里,这些新时代的山水画虽洋溢着一派新风新貌,但在另一个维度上,也失却了不少古代山水画的文化元素。1980年代之后,在当时以“虚无”论调探讨传统中国画的影响下,画家们以不同途径探寻“智者创物”般的突破契机,或放眼西方现代艺术,或追寻古代优秀传统。具体到当代山水画,一则在意蕴层面消弭了古人生存观念中的山薮林泉之思,再则在笔墨语言层面多数作品无法很好地承继传统,但对实景写生的重视也从另一角度强化了画家对真实山水的展现。当代的雪景山水画创作,也可笼统分为延续传统和强调实景两类。前者效仿古人,将五代、宋、元的雪景山水图进行现代“翻版”,在图式和技法等层面尽量靠拢古典形式;后者多对景写生,或借助媒材的探索和创新高度逼真地表现出冰雪的状貌,以画面实效肌理给人一种萧寒体验。这两类,都出现了代表性的画家与作品。 时代的迁徙确实能更易许多东西,在享受新变喜悦的同时,往往也会遭遇某些无奈流失的惆怅。就如古代雪景山水中的“比德”观念和古典文人寄寓其中的若干情思,在今天同题材作品中往往很难找寻。但在更高的标准上看,如果彻底泯灭了沉淀在山水底部的精神内质,那单纯的冰雪实景山水画又与随手拍下的雪景照片有何差异?我们确实不可追复古代文士的思想与情致,但当代也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感人的精神内质,而且找到与之对应的完美形式。这些精神内质虽不再依“比德”而出,而完全有可能与雪景山水这一千年不坠的不老神话深度相融,空灵冲默又不失时代旨趣的山水形貌和高雅深层的文化精神也并非是古人的专利。